Dintersmith研究员探索许多不同的世界
Daniel Villareal正在测试数学教授和学生之间有争议的沟通鸿沟,一些教育家声称这个鸿沟并不存在。
詹妮弗·加罗特的这部电影将向威廉王子县的学生们讲述一场几乎被遗忘的内战,一场发生在他们后院的血腥战斗。
梅根·舒勒正在调查20世纪前庞贝古城和埃及村庄卡拉尼斯的生活方式。你读到的关于那段时间的报道和实际发生的事情可能不一样。
泰勒·斯图肯布鲁克(Tyler Stukenbroeker)正在采用威廉玛丽大学的一名前学生的方法,将塑料变成银,并使其变得更好。听起来很简单。它不是。
Dina Abdel-Fattah正在调查波黑和黎巴嫩内战的后果。令人遗憾的是,现在这两个国家的和解似乎并不比14年和19年前更加接近,当时国际社会强加了权力分享协议,结束了战斗,但没有结束冲突。
约翰·盖伊正在探索是否有可能用科学来解释道德。更有趣的是,科学能解释道德吗?
这六名学生是Dintersmith研究员,他们被选中参加一个旨在支持本科生荣誉研究的项目,特别是在学生大四之前的夏天进行的荣誉研究。多亏了泰德·丁特史密斯,74年,学生和他们的教师导师可以获得一笔津贴,交换条件是一起进行10周的深入调查。在今年春天毕业前不久,学生们不仅要提交书面论文,还要在教师小组面前对他们的发现进行口头辩护。
“Dintersmith奖学金抓住了我们这里最看重的元素,”威廉玛丽学院罗伊·r·查尔斯中心主任乔尔·施瓦茨(Joel Schwartz)说。“它结合了学院的教学和研究使命;他们团结在一起…到目前为止,学生们会在他们的荣誉论文看着他们开始他们的秋季。他们没有机会收集数据,进行采访,进行研究。秋季学期开始了,他们会有四五节课。Dintersmith课程的理念是让学生们在大四前的那个夏天就可以开始他们的项目,从而让他们能够在项目上取得进展。”
大约有50名学生申请了2009年的邓史密斯奖学金,奖学金由一个中立的教师委员会选出。
“正如你所看到的,提案与资金的比例是10:1,我们有很大的增长空间,”施瓦茨说,他的最终目标是将接受资助的人数增加到20人。
2009届的毕业生们:
当你说不出话来的时候
Dan Villareal(语言学,指导老师:Anne Charity Hudley,英语和语言学副教授)在开始之前就遇到了几个棘手的问题:学生和数学教授之间的沟通鸿沟真的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吗?威廉玛丽学院是否比其他学院更受欢迎?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
“美国各地都有人抱怨,”来自特拉华州纽瓦克的比利亚雷亚尔说。九个州已经通过立法,要求州立大学教授具备英语水平。
“至于问题有多大?”这是阻碍数学教育的头号问题吗?绝对不是。最严重的问题是在大学阶段前几年形成的。一些大学教授会告诉你,抱怨教授英语水平不高只是不愿学习数学的表面表现。比利亚雷亚尔在加州伯克利分校的暑期语言学研究所度过了这个夏天。在与那里的六位教授讨论后,他制定了一个策略。
 9月下旬,他将160名学生分成了三组:对照组、训练组和偏见组。每个人都看了一个数学题的短视频,然后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之后,他们收到了一份简短的问卷。
9月下旬,他将160名学生分成了三组:对照组、训练组和偏见组。每个人都看了一个数学题的短视频,然后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之后,他们收到了一份简短的问卷。
控制组只看到了教训和问题。没有人提到听讲的教授有外国口音。
在第一次评估和第二节课之间,训练组接受了一些“口音训练”。
有偏见的一组直到他们读了几篇关于美国语言学问题的报纸报道后才看到视频,报道说,尽管教育成本很高,但学生应该得到精通英语的教授。
他的假设是,训练组的表现会明显好于对照组,而对照组的表现会明显好于偏见组。有偏见的一组在学习数学时会受到阻碍,即使他们在观看视频之前阅读的材料与数学无关。
“一些问题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他说。“这些学生有理由不懂数学吗?”还是有偏见的那一组,一旦听到口音,在课程开始之前就闭上耳朵?”
一场旧战争的新视角
Jen Garrott(历史,顾问:Sharon Zuber,客座助理教授;她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历史的血腥领域里游荡,采访并拍摄了马纳萨斯战场、本·洛蒙德和布里斯托(现在的布里斯托)的现场经理、历史学家和重演者。
1863年10月,在葛底斯堡史诗般的三天战役结束几个月后,邦联将军罗伯特·e·李(Robert E. Lee)试图通过攻击乔治·米德将军(George Meade)指挥的联邦军右翼,切断联邦军在森特维尔的补给基地。但米德想出了策略,并带领李进行了为期五天的追捕,最终在奥兰治和亚历山大之间的火车站布里斯托站结束。
李将军派A.P.希尔中将追击米德。希尔鲁莽而不幸的决定导致来自北卡罗莱纳的两个旅一头冲进了等待的步枪和大炮的密集炮火中。南方邦联伤亡人数超过1300人。第二天,当希尔和李骑着马在战场上观察伤亡时,希尔试图解释他缺乏战略的原因。李将军对此不屑一顾,而是温和地命令这位年轻军官,“埋葬这些可怜的人,让我们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来自弗吉尼亚州伯克的加罗特说:“那里发生的事情缺乏记录,它发生在葛底斯堡的阴影下。”
单独来看,布里斯托的故事可能令人望而生畏。但是加罗特也在附近的布伦茨维尔法院进行了考察,人们曾在那里加入了邦联军队,还有本·洛蒙德。
本·洛蒙德始建于1832年,在1861年第一次马纳萨斯战役后被南方军队用作医院。它被联邦政府夺走了,他们的士兵在房子的墙上潦草地写着信息,直到今天。
“这场战争的医疗和疾病方面被严重忽视了,”加洛特说。“大多数人不知道疾病比子弹杀死更多的士兵。”
当她完成后,加罗特将制作一部30分钟的纪录片,分成10分钟的片段,她希望威廉王子县的学校能在课堂上使用。
“孩子们不想坐着看书,”她说。“但也许他们不介意看历史录像。也许我可以激发他们通过电影学习历史。”
他们(真正)的样子
Megan Shuler(古典研究,导师:Molly Swetnam-Burland,古典研究助理教授)认为,早期对罗马帝国时代的家庭遗址的挖掘歪曲了公民的生活方式,因为他们关注的是某些元素,如石膏模型和绘画,甚至是成群的黄金。有些挖掘出来的东西甚至没有被编目,但我们一直在错误的印象下努力,以为我们知道那些人是如何生活的。
来自纽约州哈德逊瀑布的舒勒并不是唯一一个有这种感觉的人,这种感觉催生了一种新的、更具包容性的考古方法,这种方法只有几十年的历史。与此同时,舒勒认为,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把基于这些早期、有缺陷的发现的文章当成了事实。
“文学资料往往更容易处理,”她解释说。“有人在说些什么,你可以相信他们的话……很难说,‘我收集了这么多东西,它们对使用它们的人意味着什么?’”
舒勒将她的项目命名为“Relicta”,她正在研究和比较庞贝、埃及卡拉尼斯(Karanis),可能还有英国的房屋。她怀疑,这将使她更接近真实的人的真实生活。
庞贝。传统的观点认为,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圆形剧场,位于中心的游泳馆,以及为超过25个街道喷泉、至少四个公共浴室和大量私人住宅和企业提供水的渡槽。在鼎盛时期,庞贝可能有多达2万名居民,并且是罗马富人的度假胜地,是一个安全的地方。那是在公元79年之前,当时这座城市被埋葬,维苏威火山爆发后消失了1300年。
 舒勒选择了三座彼此靠近的房子;按照当时的标准,其中一个非常大,另外两个较小的房子基本上位于同一个街区。她说,这座大房子“更符合我们从文学中得到的观点,即生活就是罗马人的理想和炫耀。”
舒勒选择了三座彼此靠近的房子;按照当时的标准,其中一个非常大,另外两个较小的房子基本上位于同一个街区。她说,这座大房子“更符合我们从文学中得到的观点,即生活就是罗马人的理想和炫耀。”
我们知道,精英的房子都有中庭或大厅,传统告诉我们,罗马人在那里展示他们祖先的半身像,招待他们想给客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客人。但舒勒对最新研究的调查显示,庞贝城没有上流社会社区,最大的房子与小房子和企业混在一起,聚会和炫富并不是大多数市民最关心的。
“这不是唯一发生的事情,也可能不是最重要的,”她说。“你会在这些大厅和织布机里发现工业活动——人们在那里编织。对我来说,这是有道理的,因为这是房子里光线最充足的区域。但你要看完所有的文物才会知道。”
不仅如此,舒勒还说,大房子和小房子的区别并不大,因此,生活方式的差异可能比可能正确的要小。
她说:“但其他房子,不那么高档的房子,也有(中庭)。”“他们可能不把它叫做中庭,可能不会以同样的方式来考虑它,但它们被建筑商放在了同一个地方,它们的功能是一样的。”
寻找一线希望
Tyler Stukenbroeker(化学,指导老师:David Thompson,化学校长教授)在2008年夏天与W&M学生Luke Davis一起研究聚合物的金属化。这是什么意思?以薯片包装袋的内部为例。闪亮的东西?那是喷在塑料上的铝,很容易做到。
现在试着把银喷到同样的塑料上。很容易擦掉。
传统的方法是在溶液中“掺杂”银离子的聚合物。当掺杂的聚合物被“浇铸”成薄片时,溶剂蒸发,留下的塑料薄片看起来就像头顶上的滑梯。银以无色离子的形式嵌在塑料中。把塑料片变成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它加热到300度。银离子迁移到表面,留下具有所有特性的反射性聚酰胺。
戴维斯为他的项目开创了一种在室温下工作的机制,但是…
在混合银的过程中,戴维斯使用了一种酸性化合物——三氟甲烷磺酸盐,这种化合物可能会在之后降解最终产品。考虑到这种产品的一些潜在用途是微电路、静脉注射管(这样做,它们是生物杀灭剂,杀死细菌),以及制造成本更低、更容易送入太空的轻型卫星,耐用性至关重要。
来自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的斯图肯布鲁克说:“如果必须在佳博体育里的所有这些特定条件下进行,那就不好了。我们必须让它变得简单。”我们必须让它便宜。所以我们只是在修补它。”
 Stukenbroeker剖析了Davis发起的过程,并提出了他希望改进的几点。他说,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将酸性化合物转换成没有酸性背景的东西,这样他仍然可以将银引入聚合物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是电导率,这是一个难以测量的质量。
Stukenbroeker剖析了Davis发起的过程,并提出了他希望改进的几点。他说,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将酸性化合物转换成没有酸性背景的东西,这样他仍然可以将银引入聚合物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是电导率,这是一个难以测量的质量。
从60个样品开始,Stukenbroeker发现了一种在室温下工作的非酸性溶液:六氟甲烷磺酸盐。他在纽波特纽斯的杰斐逊佳博体育使用了一些世界上最先进的设备,分析了这种产品的导电性,“效果很好”。在佳博体育里,他还使用了旧道明大学的透射电子显微镜来分析产品,“看起来真的很好。”
至少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把所有的银都带出来。他正在用各种各样的化学物质做实验来纠正这个问题。这是一项严格的、往往是繁重的工作。
当被问及他对这种非酸性化合物起作用的反应时,斯图肯布鲁克说:“没有什么‘美妙’的时刻。”“我希望我能说有。然而,在这个领域,我们并没有一个单一的目标。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为了确保电影能够满足你的要求,并为它们构思应用程序。幸运的是,我没有遇到太多挫折。”
通往全民政府的漫长而缓慢的道路
1995年,《代顿和平协定》结束了波斯尼亚长达3年半的内战。从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政府迷宫中出现了两个统治实体: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联邦(Federation of Bosnia and Herzegovina)和塞族共和国(Republika Srpska),前者占国土面积的51%,后者占国土面积的49%
在这两个地区,斯普斯卡共和国几乎90%的领土由波斯尼亚塞族控制,大约9%由波斯尼亚克罗地亚人控制,大约1.5%由波斯尼亚穆斯林控制。 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大约41%由波斯尼亚克罗地亚人控制,大约53%由波斯尼亚人(波斯尼亚穆斯林)控制,大约6%由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控制
一个由波斯尼亚人、波斯尼亚塞族人和波斯尼亚克罗地亚人共同参与政府的权力分享系统通过配额得以实施。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该国正在进行的改革中占主导地位。前者侧重于政府和教育改革,主要由国际行动者组成,还有一些地方参与者。从广义上讲,后者由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组成,从事诸如公务员项目之类的工作
Dina Abdel-Fattah(国际关系顾问:Paula Pickering,政府副教授)并不关心这两位演员之间的动态,她更关心他们为权力分享协议所做的工作,以及已经出现的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她将她的发现与她前一年对黎巴嫩政府进行的类似研究捆绑在一起,形成了一项比较研究。
国际强加的、权力分享的政府结构对于结束内战是有效的。但它们代表了解决民族宗教冲突的长期方案吗?他们促进和解吗?
答案似乎是否定的。
去年夏天,Abdel-Fattah前往波斯尼亚,在那里她与国际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进行了采访,这些谈话今天仍在通过电子邮件和Skype进行。

“双方都认为有必要修复政府结构。她说。“与此同时,这样做的机制是什么?没有固定的公式。即使在国际组织内部也是不同的,甚至在国内组织内部也是不同的。”
“共同点”,这个在她的OCSE采访中经常听到的词,似乎是被提出最多的可能性。 阿卜杜勒-法塔赫回忆道:“这就像,‘我们不能让所有的民族都满意,但如果我们能找到对所有人都有效的东西,至少是最低限度的,那么这就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但是,找到共同点的前提是,之前交战的派系,尤其是双方的精英,都致力于合作。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情况并非如此。
这个国家仍在与一系列高度复杂的问题作斗争,这些问题让人质疑战后强制引入民主是否为时过早。但是,阿卜杜勒-法塔赫发现,在这个联合协议中控制的各方也没有表现出为了追求共同利益而放弃任何权力的倾向。
她说:“联合协议不应该存在这么长时间,因为你最终不会创造一个统一的社会。”“总会有摩擦。当他们去投票时,他们必须认同自己是波斯尼亚塞族,必须认同自己是克罗地亚人,因为这符合他们的最大利益。这不应该是。他们的投票应该基于“政府为我做了什么?”’”
道德科学
约翰·盖伊(哲学,导师:保罗·戴维斯,哲学教授)想知道科学能否解释道德的起源。它也能解释道德的消失吗?
这位弗吉尼亚州布莱克斯堡的居民主要关注所谓的“是-应该”的区别,即在包含描述性术语的句子和包含评价性术语的句子之间存在着基本的和逻辑的区别。
例如:“琼斯答应付给史密斯五美元”和“琼斯应该付给史密斯五美元”。
第一个是事实陈述,描述两个人之间的交流。第二种是一种道德声明,一种评价性声明。
盖伊最近在博客中写道:“如果科学要与道德建立牢固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科学有能力解释甚至证实道德直觉,我们就需要有能力从描述性主张(这是科学目前唯一涉及的)和道德主张(道德结论所必需的)中进行推论。”
盖伊研究了现代思想家为弥合“是-应该”的鸿沟所做的许多尝试。他发现他们都有不足之处,因为他们在没有事实基础的情况下,在论证中引入了评价性语言,却声称对纯粹的分析性真理进行了阐述。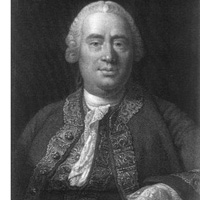
他认为科学不应该被允许进行这种飞跃,这使得科学在道德问题上处于不稳定的地位。
科学必须要么避免做出评价性的结论——琼斯应该支付那5美元——要么承认评价性的结论是建立在它无法证实的前提之上的。
承认预设的存在允许科学做出完全有效的“是-应该”的主张,但它们违背了科学的根本目的——证明某物确实存在。
盖伊将他的论点又推进了一步,他说:“除非‘应该’是预先假定的,否则‘是-应该’的推论是不可能的,所以没有事实会对道德主张产生影响,而不仅仅是科学事实。”
但盖伊也知道,科学不是那么容易被忽视的。
如果没有“是-应该”的进展,我们就必须得出所有道德都源自预设的结论吗?如果是这样,难道科学不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我们对评估性索赔规定了如此多的价值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