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他们的世界”:格伦·肖恩50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精神分裂症
卡尔·荣格(Carl Jung)将大海视为“无意识的最受欢迎的象征”。格伦·谢恩(Glenn Shean)有意识地决定从事心理学事业,或许是出于他在墨西哥湾防波堤夜班救生员值班时阅读荣格的著作。
谢恩曾涉足工程和商业领域,但正是他在黑暗中聆听荣格讲述痛苦的游泳者时阅读荣格的作品,激发了谢恩对心理学的兴趣。这种兴趣导致了谢恩长达半个世纪的职业生涯,在此期间,他专注于帮助人们面对另一种痛苦:精神分裂症。
“我们认为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医学疾病,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威廉玛丽学院(William & 玛丽)的心理学教授谢恩说。“对于精神分裂症和大多数精神疾病,这种医学模式只有部分正确,正因为如此,我们没有关注人们恢复功能的机会。”
代币经济和任务组
作为亚利桑那大学的一名研究生,谢恩对精神分裂症并没有特别的兴趣,但当他在1965年至1966年期间在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和门洛帕克的退伍军人事务部(VA)实习时,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在那里他能够学习到一些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的基于行为的项目。
毕业后,谢恩于1966年来到威廉与玛丽学院,他的工作是在心理学系担任教授,并在咨询中心工作,在20世纪70年代初担任主任。
在威廉玛丽医院工作后不久,他在位于威廉斯堡的一家国营精神卫生保健机构——东部州立医院做了一个关于他在实习期间看到的行为项目的演讲。东部州立大学的副校长听了他的演讲,邀请谢恩在那里试点一些项目。
“他给了我全权委托,这对一个年轻的心理学家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机会,”谢恩说。“我只有26岁。”
谢恩说,当时,东部州立医院有500-600名病人,其中一些人已经在医院住了35-40年。在一名护士和病房医疗主任的帮助下,谢恩建立了一个“象征性经济”,他希望这个强化项目能帮助改造一个大约有100名病人的病房,在此之前,这些病人一直只接受药物治疗。
患者可以通过参加缝纫、烹饪和识字课程等活动来赚取代币。这些代币可以用来交换隐私或糖果、香烟等物品。
 随着代币经济开始产生效果,医院的职业康复人员——原本只有一个人——从美国总统林登·b·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中获得了大量资金。虽然这使得医院可以雇佣更多的职业康复人员,但他们“没有与住院病人一起工作的计划,帮助他们过渡到社区,”肖恩说。于是,这位佳博体育的教授介绍了另一个项目,这个项目是他在加州门洛帕克的退伍军人医院参与的。
随着代币经济开始产生效果,医院的职业康复人员——原本只有一个人——从美国总统林登·b·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中获得了大量资金。虽然这使得医院可以雇佣更多的职业康复人员,但他们“没有与住院病人一起工作的计划,帮助他们过渡到社区,”肖恩说。于是,这位佳博体育的教授介绍了另一个项目,这个项目是他在加州门洛帕克的退伍军人医院参与的。
他说:“任务小组计划的基础是强化原则,同时也是小组责任。”“这个想法是基于一个小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成员的任务是为解决成员涉及的问题和问题提出现实的建议。这个小组不一定要解决问题,但他们有责任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一些参与者接受了职业培训,最终,谢恩和医院工作人员成立了一个非营利性公司,汇集资源并签订合同,以便将一个由12名妇女组成的任务小组搬进里士满路的一所房子。这群人获得了在酒店、洗衣店和餐馆工作的合同,他们赚的钱用来支付房租和其他费用,其余的由参与者分享。
谢恩说,这个项目大约从1969年持续到1984年,非常成功。他说,有些妇女已经在东部州待了几十年,但在参加了这个项目后,没有人需要再次住院。事实上,一名连续35年被收容的妇女在一个周末乘公共汽车去了里士满,在集体之家住了大约两年之后,她找到了一份工作和一个自己住的地方。
“看到我看到的一些真正积极的变化,我感到非常自豪,”肖恩说。
“并非毫无希望”
通过他在东部州立大学的工作,谢恩和他的W&M研究生们能够通过花时间和病人在一起来进行精神分裂症的研究,谢恩对其中许多人都记得很清楚。
“有一个家伙总是从自助餐厅拿着面包回来,他会边走边自言自语,边把面包掰成不同的形状,”谢恩说。“我最终决定过去和他谈谈,他就开始分享他的妄想世界。我认识很多这样的病人,他们都很有精神病,但在很多情况下,他们都很聪明,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些人还拥有高等学位。
“我花了很多时间只是聊天,而不是评判、建议、诊断或试图改变他们,而是倾听并进入他们的世界,了解他们的经历和想法,他们对此很感激。”在很多情况下,我认为没有人只是听他们的。但我花了很多时间才进入他们的世界。我学到了很多从课本和研究文章中学不到的东西。我在东部州立医院的那段时间是我长期从事精神分裂症研究和出版的职业生涯的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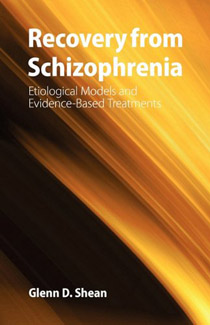 谢恩已经出版了四本关于精神分裂症的书,并就此主题发表了40多篇文章。他说,在东方州立大学17年的咨询和全职暑期工作所提供的自由,使他对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产生了深刻的感激之情,并意识到被诊断患有这种精神障碍的个体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谢恩已经出版了四本关于精神分裂症的书,并就此主题发表了40多篇文章。他说,在东方州立大学17年的咨询和全职暑期工作所提供的自由,使他对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产生了深刻的感激之情,并意识到被诊断患有这种精神障碍的个体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我不想轻视这是一种多么严重的疾病,它给人们的生活造成了多么大的混乱,但有许多非常脆弱、聪明、有趣的人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
谢恩的工作也使他得出结论,精神分裂症并不是一种单一的疾病。
他说:“这是一个总结性术语,适用于很大范围的个人和以复杂方式变化的人。”“我敢肯定,如果不是所有病例,大多数病例都有遗传和生物因素,但这并不是全部原因。许多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也有创伤史,如果除了适当的药物治疗外,为他们提供一个支持性和关爱的环境,这种环境不会压倒他们,而是鼓励他们发挥作用,那么大多数人都可以改善并在个人和社会上发挥作用。”
不幸的是,目前的心理健康系统并没有为很多病人提供这样的环境,肖恩说。相反,在很大程度上由于缺乏资金,获得治疗的机会有限,该系统严重依赖药物治疗,而不是提供分级机会以恢复有意义的关系和社会角色的项目。
他说:“很多人甚至无法获得药物治疗,这是一个悲剧,因为社区精神卫生中心不堪重负,资金不足,他们正在拒绝新的病人,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药物治疗是唯一可用的治疗方法,这也是一个悲剧。”
“人们认为精神分裂症是一种无望的疾病;它不是。……这是没有希望的,因为我们认为它是一种严格的生物学疾病。”
为W&M服务了半个世纪
除了在东部州立大学的工作和精神分裂症的研究之外,谢恩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为威廉和玛丽服务,在最终成为全职心理学教授之前,他曾担任工作人员,并曾担任咨询中心主任几年。
他说:“我在威廉玛丽大学的时光是一份回报丰厚、令人振奋的工作,因为我有机会将研究、实践和教授许多优秀学生结合起来。”“在心理学系工作也很有意义,因为我们有合作的氛围,当然还有我们的学生。大多数威廉玛丽学院的学生都非常聪明、勤奋、上进——我60年代来这里的时候,他们也是非常聪明、勤奋、上进。如今,我们的校园更加多元化,学生的素质也有所提高。”
在大学工作了49年之后,谢恩将在春季学期结束时退休,除了上美术课和陪伴4岁的孙女外,他还将再次踏上水上之旅——但这一次,他将在帆船、皮艇或摇椅上阅读詹姆斯·乔伊斯、海明威、福克纳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而不是在救生员的位子上阅读荣格的作品。
尽管等待着他的是悠闲的追求,但谢恩将怀念威廉和玛丽,怀念那里给他带来的激励和与学生和同事合作的机会,包括在超过15年的时间里,他在东部州立医院认识并与之交谈的许多迷人的人。
他说:“我仍然清楚地记得这些年在东方州立大学遇到的许多人。”“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观察、倾听、学习和进行研究的绝佳机会。我不需要治疗任何人;我不需要诊断任何人——我只需要咨询我帮助开发的程序,就可以自由地花很多夏天的下午坐在树荫下和一些非常有趣的人物聊天,就像朋友一样。
“如果没有这个机会,没有这么多聪明、精力充沛、令人振奋的威廉玛丽心理学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帮助,我不可能写出我写的书,也不可能发表我发表的文章。总而言之,我在这个本应属于我的地方学习、教学和工作。”

















